量子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红牛
缺集或无法播,更换其他线路.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最好的一课——麦收
马克思韦伯奠定了社会学中的理解(Verstehen)范式,许多社会学家在用自己的生命历程(life course)来论证这个范式,在中国,最好的三农专家本人都来自农村,就拿这个培训班上的老师来说,于建嵘,张乐天,陆学艺等。远的如费孝通先生等。或许,和时代有关,中国本来就是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然后,当我们靠近底层这样一个跨越社区的概念时,很遗憾,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不是来自底层。
底层(The grass-rooted),和基层(Local),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不一样,很多时候,他们是无名化(anonymity)或者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一群人。他们不是一般的农民,他们不是一般下岗工人,他们不是一般的妓女与鸭子,他们一定要与权力碰撞,失败后在社会中像抹杀了以后的状态。
很喜欢福柯的《无名者的生活》,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那些故事为什么重要以及为什么故事进入福柯的视野,那些卑微(infime)的人,那些无名(infame)的人。
“那些生命正在那里谈论着自身,为什么你不去听听?——但首先,如果这些生命不曾有一刻与权力相撞击,激发它们的力量,除了这些处于暴力或独特的不幸之中的 生命,难道真有什么别的东西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毕竟,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不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 生命最热烈的点,能量积聚的地方,恰恰就是它们与权力冲撞的地方,与权力斗争,努力利用权力的力量,或者力图逃避权力的陷阱。在权力与那些最平凡无奇的生 存之间往来的这些片纸只言,对于后者来说,无疑就是曾经给它们树立的唯一的纪念碑;这些文字正是投射到这些生命上的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短促光芒,它穿越时 间,甚至使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这些生命。”
“简单地说,我想要将一些残迹收集在一起,创造一部描述这些面目不清的人的传奇,它的基础就是身处不幸或盛怒中的人们与权力交换的这些文字。”
在所有呈现出研究的专家中,最贴近底层概念的是于建嵘老师的上访农民,还有就是自身没有能力,没有资源说出自己的故事的底层妓女,服务于底层民众的性工作者。前者对应污名化,后者对应无名化。
我更关心那些没有能力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们。就像法国一位历史学家一样:我的痛苦在于我不能使人民说话。沉默者的历史隐藏着历史的真相。
1、那些我们愿意或不愿意相信的
影片观毕,讨论的最多的几个问题是:红苗的男朋友和她谈恋爱的时候究竟知不知道她从事性工作,红苗的父母知不知道她从事性工作。红苗和她的几个同事讨论性交易过程细节时,知不知道摄像机的存在?和红苗龃龉拌嘴的两个男人是嫖客还是朋友?
经过思考,我的结论是:以上,我们不愿意相信的那个答案可能是更真实的。
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红苗接受访谈,红苗与男朋友卿卿我我,红苗与两个男人拌嘴都是在她唯一可以享用的一个公共交流空间——夜市烧烤摊。这就是她存在的巨大现实——她要么在炮楼里,要么在家里,要么在与鸭子一起玩乐的简易KTV 里,她和城市公共空间的交集是:医院和邮局,医院是为了自己和父亲的病,邮局是为了给家里寄钱。
生活方式与空间,是定义底层最好的方法。红苗的工资,我根据她的叙述算了一下,大概每个月3000左右,经济上她比很多打工妹要好。她有能力进行性消费。有能力出钱给父亲看病。但是,我们看到,她毫无疑问是底层。因为她毫无改变自己命运或向上流动的机会。她的生活状态与质量低于日常生活,甚至远远不如她的家乡的农民。一句话,她用身体和生命换取生活资料。
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中,红苗的男朋友之前知不知道她是否性工作者,不重要,因为他迟早知道。事实是,片子未结束,他就知道了。而且,红苗的存在,本来就是在满足底层打工者的性需求的。
注意,红苗的工作地点是炮楼(brothel),最低级的性交易地方。
最关键的那个细节,三女讨论性交易的细节,我不是卫道士,但是我由衷地感到不适,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她们竟然笑着说自己遭受的性侮辱与虐待。围绕的话题是:包夜。后面,我们知道,“包夜”是红苗们获得较高收入的一个手段。因为,单纯打炮很便宜。
让我们联系一下,那两个男人和红苗之间的龃龉,其实是因为一位男人说:你歇B吧。红苗生气了,但是我们发现,在后来,红苗对着镜头,和另一个男人模仿古典剧中,性交易双方的语言情态等。我相信,不用解释了,这两个男人都是嫖客,但是同时也是朋友。这很正常。只不过我们不愿意相信罢了。傻B的阶级分析论,以及女权论,总会把嫖客与妓女的关系想象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我把这两个细节摆上一起,是想说,底层生活的逻辑不是我们正常生活的逻辑。
那么,我来换一个场景:几个白领丽人在工余瞎侃,一个说:老板太霸道了,又给我布置了这么多任务。另一个说:就是啊,上次,也是,加班了都没有给加班费。
我没有侮辱职业女性的意思,我曾经是职业女性(留校工作过),将来也会是,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职业女性不愿意承认:性工作的女性也是“职业女性”
解构了我们的道德逻辑,我们就明白了,三个女人讨论性交易的细节,实际是述说自己的职业经历,以及自己具有获得较多收入的性资本。这和白领女性炫耀自己工作能力强被上级要求加班是一样的道理。
而红苗生气的正是,那个嫖客说了:歇B。这是对她安身立命的职业的侮辱。后面补充的镜头,正是说明,她觉得她的职业和长途司机,和其他打工都没有区别,在养家糊口的功能上。
放下道德,本身就是道德的。但不是无视或漠视。
我心痛的是,红苗在生气于无良嫖客骂她以后,她不是拂袖而去,而是说:你要是有兴趣,就打电话联系我,要是没有,就滚他妈的……
性工作者与嫖客之间是共谋(complicity)的。他们互相依存(commensalism)。这就是底层的逻辑。
记得那位劝和的嫖客的劝词吗:你有钱吗 她有钱吗 我有钱吗 那不就结了。
其实,共谋这个词,我是不认同的,任何共谋的英文都有价值判断,阴谋,诡计等。我想说,用共生吧。就像生态一样,在 底层社会里,他们有他们呼吸的小系统,排泄的小系统。
在这种“共谋”下,没有阶级对抗,没有性别政治,有的只是“为了最低级或者最基础层面上的生活和生存。”
2、一切都在消失,以我们无法预知的速度
看到红苗和鸭子之间的娱乐,我们发现,性别结构在此失效。这些鸭子们或许比红苗们悲惨。红苗至少可以还有非嫖客的情感选择,我难以想象一个正常的女性接受一个从事性工作者的男友。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男女主次二元对立结构的潜在逻辑。
性别结构,在这个底层社会的一角是消解的。
我们再来看看,红苗奔走于的城市与农村。城市,其实没有给红苗带来任何生活便利,我们看到,红苗居住的犄角旮旯,远远不如她在家乡的独立房间舒服。红苗也不可能去商场买衣服,她还是去北京与河北交界的高碑店买19元特卖的衣服。红苗的娱乐场所是另一个底层的性娱乐场所。
城市化的种种好处,对于底层的红苗来说,是虚无的。
而红苗的家乡,全家辛辛苦苦的干一年,都不如红苗在城市底层从事最屈辱的性服务来钱。
农村的极度衰败,是对中国城乡长期二元结构的最大报复。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红苗用自己的身体与青春,以一种不堪记录的方式,维系着底层的共生环境,而对于她个人来说,爱情是脆弱的,故乡如重病的父亲一样病入膏肓。未来在哪里,正如她一觉醒来,茫然面对摄影机的那双眼镜——世界有时候,在她眼里,就是那一张肮脏的床。
镜头外的我们,能够做的不是针对这一个人,而是通过她的这双眼睛,将她们和他们带入阳光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有她们的立足之地,而不仅仅是用身体换来的钱的流入与流出路途。
这是最好的一课,因为它用隐晦的方式告诉了我们底层的逻辑与真实面貌,面对同一个影片,同样的画面,我们总是相信那些我们愿意相信的。面对底层,同情,怒其不争,悲伤,都不如直面现实,来的更加尊重。投入式理解,会帮助我们去除面对残酷现实的过敏症。用底层的逻辑,情感来看待底层。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却包裹着许多,许多。
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我上培训班最大的收获。当然,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源于各位东西方大师的视角、方法的碰撞与融汇。
相关链接:
http://news.sohu.com/20050829/n226812812.shtml 李银河 卖淫非罪化
http://hi.baidu.com/249357640/blog/item/3f7e96137f1305d2f7039ead.html 基本人权背景下的性交易合法化
http://cul.sohu.com/20060906/n245196015.shtml 何兵 性交易不可能禁止 应该合法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0e190100dwsy.html 本人博客中旅游随笔 移步换景 打望渝锦 (关于重庆性工作者间接访谈)
同步发表于本人博客
2 ) 凌晨五点一点乱七八糟的想法
熬夜看完了《麦收》。看片子的时候,我在想,基本看不到构图,剪辑的手法,可能是为了表现真实。后来看资料的时候,徐导说剪辑应该全部是导演的。这就说的通了,全片就像几百t的素材堆到一块儿,从后期里再去找逻辑剪。
但是看到明晃晃的直视身份证,暴露隐私身体的时候,我感到不舒服。有人说,打码在纪录片里不算真实,但都知道,这样的镜头有很多可以避开的方法。在平衡保护人物(特别是这样的边缘女性)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天平时候,我觉得应该偏向保护被访对象,甚至可以说这些镜头属于有用的废镜头。两个小时的片子,我在导演身上很少看到对女性的尊重。是尊重,不是可怜。
看片的时候在安慰自己说,能拍出来,留下来就很不容易了。包括也有很多影评人说,知道是了解的开始。但事实是,徐导并没有在事前明确告知对方,片子的用途,在我的道德观念里,这就是不道德的。有些事情是基本,不管在哪里。也有人说,这部片子是为了让大家把j女也当做人来看,但是那么多独立电影展给了展映机会,还一直在流传,影片的初衷不像把她们当做人物,更像一群想要突破社会刻板印象的符号。当然,这就很难不让去怀疑导演有借片子抬高自我身价之疑。
(免杠,理由:可以有对立的想法,但不要试图说服。)
3 ) 在他的镜头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
有一个导演,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却整天和乞丐、妓女、老鸨这些人混在一起。
他为了拍电影,和他们同吃同住,他们被抓时,他还出钱找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
你已经很难分清,这些人,究竟是他的拍摄对象,还是他的朋友,甚至亲如家人。
他是徐童,一个1965年出生,本该和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大咖齐名,却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导演。
01
你可能都没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纪录片,虽然在国外屡屡得奖,却从没有一部在国内正式上映过。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他拍这些人、这些题材,要付出的代价。
只是他觉得比起拍那些娱乐大众的商业片,记录这些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群,更有价值。
在他的口中,这些边缘人被称为“游民”。
什么是游民?学者王学泰曾如此形容:
游民有别于草根,他们游离于秩序之外,是脱序的人群,比草根更加边缘化。
草根,可能还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虽然生活艰苦,但不至于为生存挣扎。
但游民,则是比草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为生存苦苦挣扎,不知道明天在哪。
在徐童的纪录片中,就尽是这些“游民”,他们可能是乞丐、算命的、卖身的、偷窃的……
但这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影视业最高学府之一的高材生,却偏偏放着大好工作不做,专门拍这些社会边缘人,还和他们混成哥们,自称“远看艺术家,近看是游民 ”。
他拍这些纪录片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些和我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也是中国人的游民,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他的纪录片,仿佛是一颗磨不平的沙子,留在看过的人的眼中,擦不去,也挤不出,久久地让人难受。
只要这些纪录片、这些人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忘记,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过着蝼蚁一般的生活。
02
徐童的代表作,是被称为“游民三部曲”的《麦收》《算命》《和老唐头》。
三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不同人群的“游民”。
《麦收》的主角,是性工作者牛洪苗。
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的生活费,父亲的医疗费,都是她在城里赚回来的。

做父亲的,很为这个女儿骄傲,对着镜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说红苗啊就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可以闯出来。

但父亲可能不知道的是,女儿牛洪苗,在城里做的是什么职业。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牛洪苗工作的地方——北京,朝阳区,高西店,“炮房”。
牛洪苗是一个性工作者,生活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在杂乱不堪的发郎里接待客人。
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在诺大的北京,要想找一份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养活家人,是不太可能的。
但父亲看病等要钱,母亲维持一家的开销也等着她寄钱,钱从哪来?
牛洪苗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
但她并不以此为耻,这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份工作。
工作之余,她会和姐妹们,若无其事地讨论“客人”的好坏:
哪个客人难缠,让自己一个通宵都没睡,
哪个客人像“畜生”,一晚上要搞好几次……
尽管做着出卖身体的“工作”,但像所有其他女孩一样,牛洪苗也有爱情的需求。
只不过她的男朋友,也是她的一个嫖客。
这个叫许金强的男人,同样也是一个“流民”,一个在建筑工地开塔吊的农民工,哪里有活就去哪儿,生活漂泊无依。
但他对牛洪苗却情有独钟,只见过两三回面,就天天惦记着牛洪苗,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有时候一天打三四回,东拉西扯,也没什么正经事,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就在一起了。
牛洪苗嘴上说着,让许金强不要对自己动真感情,自己只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好玩,但从眼神、肢体动作,观众都能看出来,她对许金强的依赖。
作为一个性工作者,牛洪苗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尊重人的嫖客,借着酒劲,她也会发脾气,“以后想联系打个电话,不想联系,拉XX倒”。
但遇上老板娘生日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去卡拉OK,叫上几个“鸭子”,“玩玩,图个高兴”。
在他们的眼中,这跟对男朋友忠不忠诚,没什么关系。
牛洪苗的生活,可能是更多的“性工作者”的缩影,虽然在中国,这是违法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阳光找不到的阴暗角落,仍然存在着许多像牛洪苗这样的人。
她们可能一样出生在农村,没上过几年学,进城务工,又发现高不成低不就,于是许多女孩,就从事了这样灰色的职业。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流民”。
法律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但在找到更好的生存方式之前,他们却不得不这么在“地下”卑微地活着。
03
同样身处底层的,还有《算命》中的算命先生厉百程。

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动容的,是厉百程和老伴的“爱情”。如果那也能被称做爱情的话。
厉百程是一个双腿残疾的老人,河北人,生活在临近北京的燕郊,靠给人算命养家糊口。
他的老伴——石珍珠,一出生就又聋又哑又傻,父母早亡,哥哥嫂嫂从小就让她在羊圈里住,导致她双腿残疾。
石珍珠,是厉百程四十多岁时,花一百多块钱从他哥嫂那儿“买”回来的。
生活都过不去,就更别提“浪漫”两个字。
说到为什么娶石珍珠为妻,厉百程说了四个词:“贫不择妻,寒不择衣,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婚姻关系,在厉百程看来,没什么神圣性,只不过是根据自身条件的挑选罢了:
“人贫没能耐,你还想搞好的?所以说我根本就没嫌破,就给接来了。”
但结婚之后,厉百程对妻子的照顾又无微不至,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所有家务活,他都包了,自己吃不起药,也要省下钱来,给妻子买药吃。
“我把她接来就只为我做伴侣的。”别以为穷人的世界里,就没有温情两个字,作为人,只要能吃饱饭,就有感情上的需求。
这个靠算命混日子的残疾老男人,同样有对伴侣的需求,只不过这样的需求,不一定那么纯洁无暇。
没过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厉百程嫖娼了。
导演好奇,厉百程残疾了,怎么还能嫖娼?问他:找那女人,你弄得了吗?
厉百程生气了,说:“弄不了,我收石珍珠干什么?我天天伺候她,我为了什么?”
说到底,厉百程找石珍珠,除了生活上的伴侣,也是找一个“性伴侣”。对他来说,娶个老婆,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的。
可能所有人的爱情与婚姻中,都有这样的因素,但体面的人,不会这么说出口。
只有那些生活于底层,被剥夺了尊严的“游民”,才会这样直接地面对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老了之后,厉百程也后悔过,当初不该娶石珍珠:“没媳妇,想媳妇,有媳妇,烦媳妇,当时大脑缺弦。现在是,扔不得,撂不得,现在再想和她分开,是不忍心”。
现实残酷、不堪,但即使是生存于底层的人,也同样有“不忍”和善良的心。
这就是真实的“流民”生活,他们的生活或许很卑微,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有的所有。
生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活下去,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例如,厉百程的朋友,也都是一些睡在街边的乞丐,如果没有算命这项“手艺”,他可能和那些乞丐朋友一样,风餐露宿。

导演看到这些乞丐有一顿没一顿的悲惨生活,都觉得无法理解,问厉百程:这些人活着,一点乐趣没有,为了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厉百程生气了,他说:这话说的,人没乐趣就不活着呀?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是的,对这些生活在边缘的“游民”来说,活着是没什么乐趣,但生而为人,活下去就是一种本能。
他们没有想过自杀,也没想过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些都是已经不需要为生存忧虑的人想的事。
当一个人很早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只有如何活下去,而不是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他们没时间去哀怨生活没有乐趣、没有意义,也没想过去抱怨命运的不公,社会的残忍,他们唯一想到的事,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
04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老唐头》,纪录的是老唐头的一家,主要是唐小雁,和她的父亲,唐希信。
先来说唐小雁,她是来找厉百程算命的人之一。
唐小雁是一个按摩房的老板。但她入这行,也是“误入歧途”。
17岁那年,唐小雁被一个黑老大带到田里强奸,20几岁时,她被人拿刀架着强奸。后来还被人骗到按摩房当小姐……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做过各种职业之后,没什么文化,也没啥生存技能,只认识了一些道上混的人。后来,唐小雁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按摩房。
在社会上混,她必须让自己看上去强悍一些,对上门来挑事的无赖汉,她会放狠话:“我他妈能在北京开这个店,我就不惧你。”
对纠缠她的男人,她拳打脚踢,把人赶出按摩房,把人头打破,赔了两百块钱了事。
在清醒的时候,她会对干女儿说:不要对任何男人太上心,没用,都靠不住。
但喝多了之后,她却抱着干女儿哭:“我非常非常需要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我很孤独,没有人保护我,我只能靠自己。”

这个外表凶蛮,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其实只是从年轻时就被强奸、被欺负,又没什么文化、技能,所以只能用凶悍的外表伪装自己,闯荡“江湖”。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游民”,他们生存与社会的夹缝之中,平时很少被看见,但他们确实和我们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
05
而唐小雁的爸爸唐希信,也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游民”,
因为穷,也因为脾气倔,他和全家儿女、媳妇、女婿都处不来。
老唐头和大女儿、女婿住在一个屋檐下,因为穷,只有一间房,晚上只能隔着一个帘子睡。
女儿、女婿嫌老人晚上“撸管”,吵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和老唐头闹得天翻地覆,女儿、女婿气走了。
儿子,嫌爸爸没本事,说了一句爸爸这辈子“白活了”,老唐头不干了,父子俩又吵起来,大闹一番,儿子一家也气走了。
过个年,把一家人全气走了,剩下老唐头和唐小雁两个人,冷冷清清。
人们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同样如此。
穷,最大的代价之一,可能就是不体面。
因为穷,一家人,儿子都结婚生崽了,只是只能睡在一张炕上,中间拉块布就算两张床了,没有任何隐私。
因为穷,吵起架来,子女对父母没有任何忌惮,你又给不了我什么钱,说你一句“白活了”,你还有脾气了?
因为穷,所以你必须忍受这样的生活,还必须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继续活下去的乐趣,那可能是遥远的回忆,也可能是来自女儿的仅有的一点温情。
这就是老唐头的生活。
06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牛洪苗、厉百程、石珍珠、唐小雁、老唐头这样的人。

只不过他们不会出现在新闻里,不会出现在电视剧中,也不会出现在电影院里。
他们是被忽视的一群人,蝼蚁一般,匍匐在地上,活着,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哪天会死去,悄无声息地,只是活着。
只是通过徐童的镜头,才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
通过徐童的纪录片,我们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并不是只有欢乐祥和,并不是只有美满幸福。
原来真正的底层,生活可以不堪到如此地步,原来活着,可以是件这么卑微的事。
如果这些纪录片,这些卑微地活着的人,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
或许,他们的生活有被改善的可能,或至少,他们的子女,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只是可惜,这样的纪录片,和这些“流民”一样,在这片的大地上,同样是不被看见的,它们真实存在着,却仿佛透明一样,继续卑微、悄无声息地活着。
4 ) 麦收∣妓女能恋爱吗
2008年有两大事件,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这些东西渗透进纪录片里也是自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跟这些有扯不断的联系。但我们这些普通人,既不会因为灾难过分悲痛,也不会对盛会持续热情。完全是旁观者,路过显眼的什么,瞅一眼,接着过。
主角洪苗在片中数次往返于河北老家和北京城郊,你与她擦身而过甚至不会多瞅一眼。印象中妓女特有的浓妆和袒胸露乳的装束并没有出现,她就穿着最普通的T恤和牛仔短裤,跟她的小姐妹们像聊家常一样指点着嫖客们的做派。这个不好,坏极了。那个还好,那个还好。在电话里跟嫖客讨价还价,没有什么娇软的对话,只有一句,「你别跟我较真,能等就等,不等拉倒」,一副江湖儿女的理直气壮。聊起她最好的姐妹,那个叫格格的同道中人,说「你别瞧她外表看起来特别厉害,对待客人毫不客气,但只要一个神秘人物打来电话,她立刻化身成为最柔软听话的小女人」。这话多么耳熟,我们平时谈起哪个女生,好像也常这样讲。
镜头还真捕捉到了这个画面。两人在出租屋外的水池子底下洗衣服,格格看到那个男人的来电,紧张到站不直,嘴里嘟囔接还是不接接还是不接,哎呀接了又能怎么样,啊呀,没等我接他就挂掉了哈哈。
洪苗的男朋友也就是曾经的客人,在附近的工地开塔吊。那个瘦弱清秀的小男人让洪苗的眼睛放光,两人在路边的脏摊儿上吃饭,他喝酒她饮料,有一搭没一搭的调情。也不乏分别后频繁的来电。「他有时候一天能打三四个电话,也不说什么,就瞎聊。」洪苗笑说。
这个男人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里是洪苗从妇幼保健院拿回让人松了口气的体检报告。大太阳底下小跑过去,拿出报告让他看。他抬起眼睛说了一句,「好,你多保重啊」。这话真有分别的意味。
然后大雨,在河北的老家。男人打来电话。
你老人家过得可好啊。
好啊。
妈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妈妈做什么都是好吃的。在家吃咸菜都香。
对头。
调侃的两人哈哈大笑。然后话锋一转,男人说,
「我就是你生命的一个过客。你高兴就行,哪怕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我也愿意。」
洪苗脸色骤变,提起父亲的重病,加上窗外的倾盆大雨,她突然不再笑了,捂着脸哭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徐童问。「他嫖去了,找别人了。」轻描淡写,再无下文。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背叛更讽刺。
恕我无知,问妓女能不能恋爱。当然是能,但我却非常困惑。一个又一个标签就是一个又一个人性的枷锁,这些锁子让我们所见非人。眼里的都不是「人」,而是符号。而谁又愿意剔除一切去问一个妓女的灵魂,问她是否爱过是否痛苦过。有那点闲工夫,还不如去吃碗饺子有益。
生而为人,自身难保。耻笑你并非有心,因为还有更重的人生要过。
又是一年麦收时,一切如常,一切无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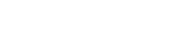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靠 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 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 笑着看 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 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 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 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 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 都是多好的人啊 太残酷了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 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无视那些道德不道德的讨论吧。。。贴着拍,就像贴着写。。。多年之后想修改下:大概还记得当年的纷争。主要是麦收的女主角之一,认为片子的拍摄和放映对她造成伤害,要求不要放映,其实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想起来纪录片界有一种观点,大概是电影无罪论,我不能同意。虽然作为电影放映员,和导演们喝出了感情。不管导演以何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环境,(无意对p客这个身份进行judge,但是这个身份,确实影响了性工作者对摄像机的态度,是存在权力关系的。至于导演后来如何尽力花钱捞唐小雁,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唐小雁的生命力很强悍,跟徐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个“救风尘”的故事。毕竟婚姻不是什么值得追寻的事物,如果这是唐小雁想要的,那徐童这个行为也算完成了一点对摄像机原罪的救赎。只是麦收里的女孩子,就真的依然在尘埃里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 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 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 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 心酸 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